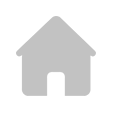内容提要:沉默权是被告人的一项要紧的诉讼权利,它是被告人的防御权、人格权,是对国家权力的制约权;它具备体现刑事诉讼价值、丰富刑事诉讼职能、达成刑事诉讼结构公正、健全刑事诉讼证据规则有哪些用途;没沉默权的权利体系是不完备的权利体系。本文试图对沉默权若干基本理论发表自己粗浅的怎么看,以期对国内确立沉默权规范尽绵薄之力。
目录:1、沉默权的由来和近况
2、沉默权的意思
3、在国内确立沉默权规范的必要性
4、沉默权的限制
5、结论
关键字: 沉默权 沉默权规范 必要性 限制
正文:
1、沉默权的由来和近况
沉默权从产生进步至今,历程了几百年的时间。而事实上古罗马法关于自然正义的司法原则就包括了沉默权的内容,“正义从未呼唤其他人揭露我们的犯罪”;教会法中,12世纪的圣·保罗曾明确指出:“大家只须向上帝供认我们的罪孽,而无须向其他其他人招供我们的罪行”。在英国,关于争取沉默权的斗争最早可追溯到12世纪早期,教会法院实行纠问式诉讼,法官有权根据教会法定罪的规定,需要被告人忠实地回答法官的提问,并作承认犯罪的宣誓,不然,将对其定罪判刑。出于维护人格尊严,被告人本能地反对如此做,并与教会法院展开激烈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普通法院出于自己利益的需要,也抵制教会法院推行承认犯罪的宣誓程序,在客观上就对被告人反认罪宣誓的斗争起到了配合用途。即这种斗争与教会法庭中适用的纠问程序和普通法院适用的控告式程序之间的斗争是紧密地联系在一块的。
沉默权在英国最早被确立于17世纪。欧洲文静复兴之后的启蒙运动,使英国社会开始看重个人的权利,人权意识开始觉醒。立法者们认识到,当个人遭到代表国家的司法机关追究时,其地位明显处于劣势,若不对其权利进行特别的保护,则司法公正在根本上很难保证,而冤假错案将会严重干扰民众对法律规范的信赖,影响社会稳定,最后危及统治秩序和统治利益。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英国发生了一块在人类法制文明史上具备里程碑意义的案件--1639年约翰·李尔本案。这促进了1642年英国议会通过了“沉默权”的法案。1898年英国的《刑事证据法》明确规定被告人享有沉默权,该证据法称沉默权为不被强迫自证其罪的特权。从此,在人类法制史上首次出现了旨在维护受刑事指控人在审讯中不说话自由的法律。沉默权的确立,被觉得是“人类在通向文明的斗争中非常重要的里程碑之一。”
其后,美国在通过的《联邦宪法修正案》第5条中规定:“其他人在刑事诉讼中不能被强迫自证有罪。”该修正案经过1963年的“米兰达案件”审判,其基本原则及操作程序得到进一步明确和健全,形成著名的“米兰达规则”。今天,不论是英美法系还是国内法系的国家,几乎都在刑事诉讼法中将沉默权确立为被告人的一项基本诉讼权利。如德国刑事诉讼法第136条a项,日本刑事诉讼法典第311条第1款,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116条,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第210条等等。除此之外,加拿大、保加利亚、波兰、等国家也有关于沉默权的规定。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3条(3)g项等都有关于其他人不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或沉默权的规定,这充分表明沉默权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
2、沉默权的意思
沉默权,又称反对自我归罪特权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一项诉讼权利。美国学者克里斯托弗·奥萨克觉得,沉默权包括以下三层含义:1.被告人没义务为追诉方向法庭提供任何可能使自己陷入不利境地的陈述和其它证据,追诉方不能采取任何非人道或有损被告每人格尊严的办法强迫其就某一案件事实作出供述或提供证据;2.被告人有权拒绝回答追诉官员或法官的讯问,有权在讯问中一直维持沉默,司法警察、检察官或法官应准时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此项权利,法官不能因被告人沉默而使其处于不利境地或作出对其不利的裁判;3.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权就案件事实作出有益于或不利于我们的陈述,但这种陈述须出于真实的意愿,并在乎识到其行为后果的状况下作出,法院不能把非出于自愿而迫于外部强制或重压所作出的陈述作为定案依据。
该项原则实质上赋予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两项权利:一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于是不是陈述享有不受强迫的权利;另一项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于是不是陈述提供不利于己的陈述享有选择权。
在国内沉默权是指在无罪推定的原则之下,当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针对侦查职员、检察职员、审判职员的讯问时,享有拒绝回答、维持沉默的权利。它是在刑事诉讼中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一项尤为重要的防御性权利。
3、在国内确立沉默权规范的必要性
在国内,关于是不是确立沉默权规范一直存在着争议,赞成者有之,反对者亦大有人在。大家觉得在现代法治国家的法律理念中,司法机关作为国家机器,作为公法人,在执法时是不允许犯了错误误的。由于这类机构本身代表着社会公正,其职责就是要尽力维护法律的尊严和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受非法侵害,假如他们执法的程序违法,一方面亵渎了法律,其次也损害了公民的利益,这被觉得是比普通公民的违法要紧急得多的事情,是不可原谅的,也因此要承担较为紧急的法律后果。
国内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与1979年的《刑事诉讼法》相比,进步非常大。突出了保护被告人、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的内容,但并未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沉默权,相反却在该法第9条中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职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这与联合国《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公约》的最低标准有较大差距,由于国内已经加入了该公约。依据国际、国内状况,大家觉得有在刑诉法中规定沉默权的必要。
第一,确立沉默权规范事实上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宪法权利在刑事诉讼中的体现。沉默权的本质是人权,是平等,每个人都享有人格尊严、意志自由和言论自由的权利,而言论自由的权利体目前刑事诉讼活动中,就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自愿供述的权利,也有缄默不语的权利。沉默权是现代法治国家刑事司法规范的一项要紧内容,反映了一个国家在刑事程序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情况和刑事诉讼文明进步的程度。但在国内司法实践中,在法院判决之前,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沉默总是被觉得是“抗拒”,办案职员或许会不惜所有方法让其“招供”,刑讯逼供也就应运而生。在此情境之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可能就是以牺牲其人格尊严和言论自由的权利甚至是被迫捏造客观事实为代价的。只有确立沉默权规范,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才可以得到进一步的保障,同时,也促进诉讼规范的进一步法治化。
第二,确立沉默权规范是国内履行国际义务、与国际接轨的需要。1998年十月,中国正式签署加入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该公约第14条规定:“受刑事追诉的人不能被强迫作不利于我们的证言,或者强迫承认犯罪。”这就是沉默权中不自证其罪的原则。国内已签署加入的《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第7条规定,少年刑事被告人在诉讼的每个阶段应享有“维持沉默的权利”。国内应付已参加的国际条款的规定有积极遵循的义务,但现在的情况是,国内在国际刑事司法活动中支持沉默权,而在国内司法活动中对沉默权持否定的态度,这是自相矛盾的。只有在国内法中明确沉默权,才能维持法制的统一性。
第三,确立沉默权规范是无罪推定原则的势必需要。国内《刑事诉讼法》第12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其他人都不能确定有罪。”这一规定使无罪推定原则在国内得以确立,即“判决产生罪犯”,这是司法观念更新的标志,是新的刑事诉讼模式的基础,也是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诉讼地位的依据。但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权作保证的无罪推定原则是不充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人民法院判决有罪之前享有独立的人格尊严,具备与控告方平等和独立的诉讼主体资格,《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审判职员、检察职员、侦查职员需要根据法定程序,采集可以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证明其有罪的责任依法由控方承担,被告人不承担指控自己有罪的责任。这里的沉默权不止是无罪推定原则的核心内容,更是诉讼程序正义的要紧体现,程序正义是公正的实体裁决的保证,特别是被告人被法院认定有罪之前的人格尊严的保障。没沉默权规范的保障,无罪推定原则则是空中楼阁。
第四,沉默权规范是达成控辩双方地位平等、推行控辩式庭审模式的要紧条件。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打造了控辩式的庭审模式,公诉人从居高临下的地位回到与被控方平等的地位,法官居中裁判,被告人在被法院定罪之前与控诉方处于一种平等的地位。既然是控辩式的庭审模式,就意味着诉讼中控辩双方的对等性,公诉方当然不能强迫受控诉一方帮助自己追究其刑事责任,不然就不会有平等与公平。但在实质的刑事诉讼中仍带有浓厚的纠问式色彩,诉讼的双方却是不平等的,这与没规定沉默权和需要被诉方“如实回答”的义务有关。被告处于被纠问和如实陈述的地位,何来平等的控辩式。与拥有国家强制力作后盾的公安、检察和法院相比,对实质处于弱势的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赋予其沉默权,平衡控辩审三方地位,也体现了司法规范中的人道精神。
第五,沉默权规范能够帮助抑制刑讯逼供的违法行为,保障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人身权利。制止刑讯逼供是沉默权在刑诉程序上的反映,虽然《刑事诉讼法》规定了“不轻信口供”和“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与其他非法的办法采集证据”的规定,但囿于司法队伍的素质、侦破技术和方法的落后及办案经费的匮乏,侦破工作总是重口供、不重其他证据,或由口供引发其他证据。因此,刑讯逼供获得口供的现象一直是司法范围的顽疾,长期禁而不绝,再加上《刑事诉讼法》第93条“犯罪嫌疑人对侦查职员的讯问,应当如实回答”的规定,既然法律需要犯罪嫌疑人承担如实陈述的义务,其反面的影响就可能导致甚至放纵违法审讯,想尽所有方法去获得口供,难免刑讯逼供,侵犯犯罪嫌疑人的人权。《刑事诉讼法》第93条规定如实陈述的义务不只与沉默权相悖,而且司法实践中因为侦查职员对犯罪嫌疑人是不是“如实回答”的主观判断的随便性,因此诱供、逼供的状况并不是非常偶然。虽然沉默权的确定并不可以全然遏制刑讯逼供的恶疾,但免除犯罪嫌疑人如实陈述的义务,从规范上能够帮助抑制并消除警察暴力,免除因不“如实回答”而可能产生的刑讯逼供、冤假错案的恶果。培根说过:“由于一次犯罪污染的只不过水流,而一次错判污染的却是水源。”铲除“毒树”的成长根源,其重要程度更甚于踢除“毒树之果”。
沉默权现在在中国虽然还是一项比较奢侈的权利,但打造它应该只不过时间的问题。事实上,沉默权已经开始进入中国。中国正式签署加入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从法理上讲,这类国际条款虽然不是国内国内法的范畴,但也是国内的法律渊源,具备与国内法同等的法律效力,对国内的国家机关和公民具备法律效力。
4、沉默权的限制
任何一项规范都不是尽善尽美的,沉默权规范也有其自己的缺点,其科学性尚需研究。在沉默权规则之下,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愿供述而一直沉默,在一定量上会干扰指控和定罪的效率,特别是当沉默权被滥用时,其导致的效率损失更是十分紧急;而且,当事人行使沉默权也大概存在非法目的,如在一些恐怖主义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和毒品犯罪案件中,沉默权的行使会帮助罪犯逃避法律的制裁,致使更大的不公正,因此有的学者觉得实行沉默权弊大于利。另外,有的案件中犯罪嫌疑人享有沉默权并滥用之,“打死我也不说”,案件就无从侦破。
因此,国内在确立沉默权规范的同时,也有必要对其进行一定量的限制。针对国内现实情况,考虑到公共安全,大家觉得应将以下几种犯罪作为例外状况而限制沉默权的行使。
贪污、贿赂犯罪。此类犯罪主体多为党政官员,学会着处置公务的权力,基于这类权力,他们在社会上处于优势地位。需要这种类型的人承担与其权力相适应的职责以外的更多义务也是适当的,这种义务包含廉洁义务,即需要其因贪污贿赂罪被追究刑事责任时,不享有沉默权,需要说出事情的真相。实践中,这种犯罪主体都是有职权的人物,大都具备肯定的文化程度和让人羡慕的职业、职务或社会地位,活动范围广,活动能力强,社会关系网多,作案前有筹备,作案后有对策,有较强的反侦查能力,常干扰侦查活动。他们总是使权钱买卖发生在合法实行公务中,使侦查取证难。基于此,有学者觉得贪污贿赂犯罪应成为拒绝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的例外,且其回答义务可以延至审判阶段。不然,以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或伪证罪或拒不作证罪被处罚。
有组织团伙犯罪。有组织团伙犯罪具备人数多、组织严密、结构稳定、管理规范、风险性大等特征,有些甚至直接危及到国家政权,因此,各国对有组织团伙犯罪都采取特殊的刑事政策。“二战”后很多国家觉得,轻刑化倾向“不适合适用于对黑社会组织活动的处置”。因此,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可以规定证人尤其是黑社会性质组织中的共犯和知情者的如实作证的义务,拒绝作证的应予处罚。但此例外状况应结合法律化后的“坦白从宽”规则及证人保护规范来实行。
公共安全及抢救犯罪。对不立即讯问并获得供述就可能导致公共安全重大风险的,犯罪嫌疑人不立即提供受害人所在场合就可能危及被害人安全的犯罪嫌疑人不享有沉默权。这种案件包含危险品下落不明的投毒、枪支弹药、爆炸品犯罪;能引起一系列伤害事件的政治谋杀犯罪;可以导被害人死亡的绑架犯罪等。
以上例外状况的沉默权合理限制用首要条件需要是发现了有关职员可能是犯罪嫌疑人的相应证据。这个证据并不要达到定罪或起诉标准,只须能引起“常人的怀疑”就能。对于出现例外状况,假如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拒绝合作,那样他的沉默权应作为对其不利的判断,其沉默行为本身应被刑法处置。只有进行了这类合理限制,沉默权在中国才能在不给社会导致较大冲击的状况下得到推行。
5、结论
综上所述,沉默权在被告人的权利体系中,处于基础性的地位,是一种优先于其它权利的权利,是其它权利的基础和保障,没沉默权,其它权利将没办法达成或者没办法充分的达成,没沉默权的权利体系是不完备的权利体系。所以,沉默权是被告人不可或缺的诉讼权利,只有规定沉默权,才能真的体现出现代诉讼理念中的公平、正义,即公正。
笔者相信,伴随国内司法规范改革的深入,对人权保护的进一步看重,在不久的以后国内的法律上也会出现沉默权,当然,这中间会出现很多问题,但大家不可以由于怕失误而拒绝尝试和努力。只须结合中国国情,吸取古今中外有关沉默权原则的合理原因和科学办法,相信国内有限制的沉默权规则会发挥积极推动作用的。国内的法律规范也将日益健全,赋予犯罪嫌疑人的沉默权,不再是奢侈品,而是司法文明的体现。德国法学家耶林说得好,“世界上的所有法都是经过斗争得来的。所有要紧的法规第一需要从其否定者手中夺取。无论是国民的权利,还是个人的权利,大凡所有权利的首要条件就是时刻筹备着去倡导权利。”
参考书目:
夏继松:《试论沉默权规范在国内的限制适用》,载《安徽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第2卷。
戎百全:《论沉默权及其法价值》,载《浙江万里学院学报》2003年3月第16卷第1期。
刘金友主编:《证据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梁慧星主编:《为权利而斗争》,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
中国政法大学 法学院
沉默权的立法考虑
点击数:182 | 发布时间:2025-02-05 | 来源:www.outfolk.com
- THE END
声明:本站部分内容均来自互联网,如不慎侵害的您的权益,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
-
- 学习交流 -
-
欢迎加入中国人事人才网,与万千考友一起备考

- 成考路上不再孤单
专业院校
-
关注“考试直通车”
-
领取备考大礼包
-

点我咨询
返回顶部
Copyright©2018-2024 中国人事人才网(https://www.xftgo.com/)
All Rights Reserverd ICP备18037099号-1

-

中国人事人才网微博
-

中国人事人才网